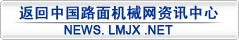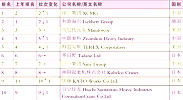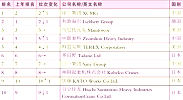新新歐洲人
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之後,北方鐵幕後的歐洲人充滿熱情和能量。10年之後,當年那些新歐洲人的升級版是中國人。
“吊車吊起集裝箱,往輪船上運,集裝箱在空中搖擺,吊鉤很難控製它的擺動。箱門沒有關好,突然敞開,像下雨一樣掉下來十幾具屍體。以為是櫥窗裏展示用的人體模型,但掉在地上的時候,腦袋像真人頭骨一樣被砸開花。那確實是人的頭骨。從集裝箱裏掉出來的是男人和女人。死人。冰凍起來的屍體。一個一個摞起來,像是罐頭裏的鯡魚。他們是永遠不死的中國人,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們之間轉手。現在知道他們去了哪裏。”
這個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場景描寫來自意大利小說家薩維奧諾所著的暢銷小說《那不勒斯的黑手黨》開篇。
這並不是中國人在意大利唯一的“恐怖故事”,就連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也曾經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宣稱,“中國人用嬰兒來做肥料”,為此,貝盧斯科尼所擁有的AC米蘭隊中國球迷還被嘲諷為“肥料”。不過,貝盧斯科尼素以大嘴和愛亂說話而著稱,所以並沒有多少意大利人真正把他說的話當回事。但在歐洲一直流行著一個說法:一個中國移民自然死亡後,其他的非法移民就會頂替死人身份。這個明明是虛構的故事,卻被不少意大利人當了真。一方麵,這本銷售過百萬的暢銷小說被列入“非虛構”類作品,另一方麵,它十分符合很多意大利人心目中中國人的行為邏輯:極端現實,極端實用主義,因為沒有宗教信仰而不敬鬼神。
當時還在意大利莫羅拉機械技術有限公司擔任大中華區總經理的鄧京紅也聽到了這個故事,她身邊還有不少意大利朋友向她求證,當她質疑這種說法時,有朋友甚至嚴肅地對她說,“鄧,我知道你是中國人,但你也要尊重事實,不要沒原則地為中國人辯護。”
工學博士鄧京紅最後心平氣和地分析道,如果這件事是真實存在的,那麽它應該首先從當地的報紙、電視台被爆料出來,然後再傳播到文藝作品,但事實上,除了這本小說之外,從來沒有看過任何媒體對此事有過報道。
這個理由說服了不少意大利人,但是“不死的中國人”的故事,還是成為了更多意大利人相信的事實,甚至傳播到整個歐洲。據說,這本小說已經被美國購買拍攝影視劇的版權,別忽視這本通俗小說的傳播力,黑幫故事是意大利的文化標簽,過去十年間,美國影響力最強的電視劇不是中國人相對熟悉的《老友記》、《絕望的主婦》這些劇目,而是HBO以一個意大利黑社會分子家庭生活為故事背景的《黑道家族》(The Sapraros)。
意大利影響力最大的報紙《晚郵報》的資深記者拉菲爾·歐利阿尼也對這個故事產生了興趣,他決定用自己職業的調查采訪來求證這一說法的真實性。說到中國人,這個荒誕不經的說法在各種文化層次的歐洲人那裏都有市場,剛剛說服一個人,又有十個人開始相信。
歐利阿尼出生於意大利東北端的小城的裏亞斯特(Trieste),在“翡冷翠”式的意大利城市譯名中,它叫翠絲緹。這個城市離斯洛文尼亞隻有一河之隔,從小他就記得,為了讓斯洛文尼亞人感受到基督教的宗教感召力,意大利政府在市中心建了一座河對岸也能看到的教堂,這座為了意識形態鬥爭而趕製出的教堂遠遠沒有古典建築的雋永,所以被他稱作“醜教堂”。
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之後,他認識了北方鐵幕後的歐洲人,他們充滿熱情和能量,推開小酒店的門,這些人眼睛在黑暗中發著光,低聲唱著政府禁止傳播的搖滾歌曲。飽含著激動,他寫下了他的第一本書《去北方》(To The North)。但是10年之後,他發現這些當年的新歐洲人已經變得跟他們這些老歐洲人一樣,死氣沉沉,滿腹怨言。
接下來,他又發現了當年那些新歐洲人的升級版—中國人。“由中國人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輕的,而由意大利人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從表麵上看已經老了。”歐利阿尼在書的第一段這麽寫道。他們的能量看起來更加用之不竭,但中國人的能量隻指向一個單一的目標:賺錢和存錢。
更讓歐利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們怎麽能存下那麽多錢?意大利是個發達國家,2011年人均國民收入2.3萬歐元,在歐元區排第五,有經濟學家認為,加上漏稅的灰色收入甚至可能排第一,這些收入能夠讓他們保持高品質的生活,但高稅收和高消費讓他們也很難有多少積蓄。
而一個典型的意大利中國勞工都是從負資產狀態開始的。真正的負資產:因為付不出偷渡的15000到30000歐元,他們必須無償為雇主打兩三年工,然後才能開始領到工錢。盡管如此,他們一般也能在5年之後存上幾萬歐元,然後盤下一個小店開始經營。
歐利阿尼認識了一對浙江夫妻,了解他們的生活,夫妻倆夏天不開空調,冬天不開暖氣,每天吃飯決不超過10歐元,一個月隻花400歐元,幾年後就存了4萬歐元。“400歐元,4萬歐元!”歐利阿尼用了一個誇張的表情來輔助表達他的驚訝:“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麽。”
“當然,我認為中國人願意如此辛苦,是因為他們覺得能改變,而我們意大利人則認為,如果今天辛苦,那麽十年後會更加辛苦,所以我們還不如從現在就開始享受。再說了,我們就算再辛苦,也沒法像你們中國人那麽能存錢。”
就算如此他們也存不了那麽多錢,但是他們可以借錢。“而我們意大利人很難借錢,雖然我們的家庭關係很親密,但是談到錢,對不起,還是得算清楚點。”我想起來,意大利人發明了銀行、保險、複式記賬法,這個社會運行在契約之上。
“中國人靠著關係就能借到錢,這對你們中國人來說很平常,對我們來說實在太新鮮了。”我不得不糾正他說,其實這種民間借貸行為在中國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有,主要是以浙江為主。歐利阿尼則承認,他采訪過幾百個中國人,絕大部分是浙江人、福建人,對其他地方的人所知甚少。
20世紀40年代,凱恩斯年輕的弟子拉姆塞希望用一個最簡單的指標來揭開人類社會財富持續增長的奧秘。最終他找到的是:儲蓄與消費,沿著黃金比例發展的社會將持續增長。
中國儲蓄太多,消費太少,而意大利人消費太多,儲蓄太少。
意大利人在反思。“看著他們,就像在哈哈鏡裏看見我們自己,但我們已筋疲力盡、懶惰、頹廢、恐懼,在我們麵前的移民,還有著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氣,有著我們在黑白影片裏那健壯和敏捷的生硬。”歐利阿尼在他的書《不死的中國人》裏這樣描繪中國人。中國人讓他想起了他那些在上世紀50年代創造了意大利經濟奇跡的父輩們,但是又不完全一樣。
中國人也在通過意大利人審視自己。這本書的譯者鄧京紅女士20年前去意大利學習機械工程,獲得博士學位後開始為意大利企業工作。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邂逅並翻譯了這本書之後,她更多地開始審視自己的人生,“好多意大利人這輩子就是溜達著就過去了,而我們一直在爬坡,爬的時候就跟不過了似的,爬完之後才發現風景也都錯過了。”
現在,她也在試著“溜達溜達”。2011年,在辭去意大利莫羅拉機械技術有限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的職務後,她開了一間在中意之間從事商業谘詢的公司,每年一半在意大利,一半在中國,這兩個國家之間六小時的時差倒還好說,但兩邊生活速度的巨大差異,仍然讓她難以適應。歐洲隻比我們慢7個小時,但我們卻感覺身處兩個時空。隻要能沉下心來,就很難不羨慕他們的慢,很多細節在慢中才得以呈現。而意大利人則羨慕我們的快,我們的活力。
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和意大利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物種,我們隻是處於不同代際間的循環。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曾經給過財富一個定義:能在未來減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資本和承諾。這句不那麽容易懂的話被在意大利的溫州人精準地詮釋了:他們拚命,是為了讓下一代人不用那麽拚命。意大利人的父輩又何嚐不是如此,今天的從容,是當年的辛苦換來的,而我們現在的倉皇,也將為未來賺取一些閑適。
隻是這種人生轉換的代價未免過於高昂,歐利阿尼訪問過所有的溫州商人,都對為自己當年給孩子和家庭的時間太少而感到遺憾。但是他又問,如果能夠重來一次,他們會改變嗎?
“沒有辦法,沒得選擇。”大部分溫州人這樣回答。
在長安歐洲設計中心,我問來自意大利的副總經理Stefano Carminati和來自希臘的Andreas Zapatinas,他們在中國見過的最美的東西分別是什麽。Stefano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他有天晚上遇到一對挑著擔子的年輕夫婦,他們很窮,但卻夢想以後能開一家店,然後再開成連鎖店。這樣的夢想,哪怕隻是想想,在歐洲都十分稀缺;而Zapatinas則告訴我,他在中國見過最美的事物是重慶夜晚的粑粑舞,那些跳舞的大媽們雖然上了年紀,但仍然充滿了活力。
我們與意大利人各自都擁有彼此珍視的東西,很難比較什麽更好,不過相同的是,我們眼中對方各自最寶貴的東西,都跟人有關。